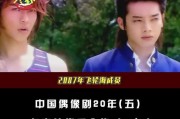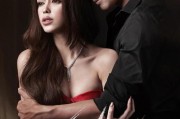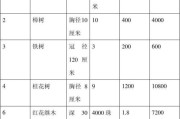壮哉:一种被遗忘的生命美学

"壮哉"二字,在现代汉语中已渐行渐远,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表达。我们习惯了"厉害"、"牛逼"、"绝了"等快餐式的赞叹,却忘记了汉语中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既雄浑又深邃的情感表达。壮哉,不仅仅是赞叹之词,更是一种生命美学的体现,是对宏大、崇高、悲壮之物的本能敬畏与由衷礼赞。这种情感表达的式微,折射出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某种萎缩——我们越来越难以被真正震撼,越来越吝啬于表达由衷的赞叹,越来越失去对伟大事物的感知能力。
追溯"壮哉"的语源,我们会发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"壮美"审美一脉相承。在《文心雕龙》中,刘勰论及"风骨"时写道:"壮者,风云之气也。"这种壮美不同于柔美、优美,它包含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古代文人登高望远,面对大好河山,不禁脱口而出"壮哉山河";太史公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评价项羽自刎乌江时写下"壮哉羽之为也",正是对这种悲壮英雄气概的更高礼赞。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里,始终为这种壮美保留着一席神圣之地,他们通过"壮哉"这样的表达,传递着对超越性存在的敬畏与向往。
在当代社会,"壮哉"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情感表达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解构崇高的时代,一切宏大叙事都被打碎,一切高尚情感都被怀疑。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碎片化的表达,表情包和 *** 流行语取代了深沉的情感交流。当人们面对真正壮观的景象时——无论是自然的鬼斧神工,还是人类的伟大创造——之一反应往往是掏出手机拍照,而非静默感受;即使发出赞叹,也多是千篇一律的"太美了"、"好震撼"等贫乏词汇。"壮哉"所代表的那种全身心投入的审美体验,那种将自我融入宏大存在的心灵震颤,在当代生活中变得稀缺而珍贵。
"壮哉"表达的衰落,实质上反映了现代人精神高度的降低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"轴心时代"理论,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,人类在精神层面实现了突破性发展。那个时代的中国,正是孔子感叹"巍巍乎,舜禹之有天下也"的时代,是庄子笔下"天地有大美而不言"的时代。而今天,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但精神相对贫乏的时代,人们忙于追逐可见的利益,却忽视了培养感受伟大、表达崇高的能力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"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",强调的正是人在宇宙中的渺小与思想的伟大。而"壮哉"这样的表达,恰恰是渺小的人类面对浩瀚宇宙时发出的思想强音。
重拾"壮哉"的表达,实际上是重拾一种生命姿态。当我们在黄山之巅看到云海翻腾,若能由衷感叹"壮哉此景",那一刻我们的心灵便与天地相通;当我们阅读历史,为文天祥"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"的气节所感动,道一声"壮哉文山",我们的精神便得到了升华。这种表达不是简单的怀旧,而是对生命维度的拓展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写道:"美将拯救世界。"而壮美作为美的一种高级形态,更具有净化心灵、提升境界的力量。每一次真诚的"壮哉",都是对平庸的一次超越,对狭隘的一次突破。
在个人层面,"壮哉"的复兴意味着审美能力的提升和精神世界的丰富。一个能够被真正壮美景象所打动的人,必定是一个心灵敏感、情感丰富的人;一个能够自如运用"壮哉"等表达的人,必定拥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情感表达能力。在社会层面,"壮哉"精神的回归则可能带来公共话语的升华。当我们的社会赞叹语不再局限于"给力"、"点赞"等平面化表达,而能重新欣赏并言说那些崇高、伟大、牺牲、奉献的价值时,这个社会的精神品质必将得到整体提升。
壮哉,不仅是一个词语,更是一面镜子,照见我们内心的深浅;是一把尺子,衡量我们精神的高度。在这个快节奏、碎片化的时代,或许我们更需要放慢脚步,重新学习感受那些值得一声"壮哉"的事物——无论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,还是平凡生活中闪现的不凡精神。唯有如此,我们才能避免精神世界的荒漠化,才能在物质丰富的今天,同时成为精神的富有者。
壮哉,这种表达本身!它承载着汉语的厚重与优美,延续着中华文化中对崇高美的追求。在未来的岁月里,愿我们不仅能在词典中见到这个词,更能在生活中听到它,在心灵中感受它。当"壮哉"重新成为我们情感表达的一部分时,或许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壮阔而深邃。
 资讯网
资讯网